語文教學浮想錄
文/劉漢初 小語匯第四十三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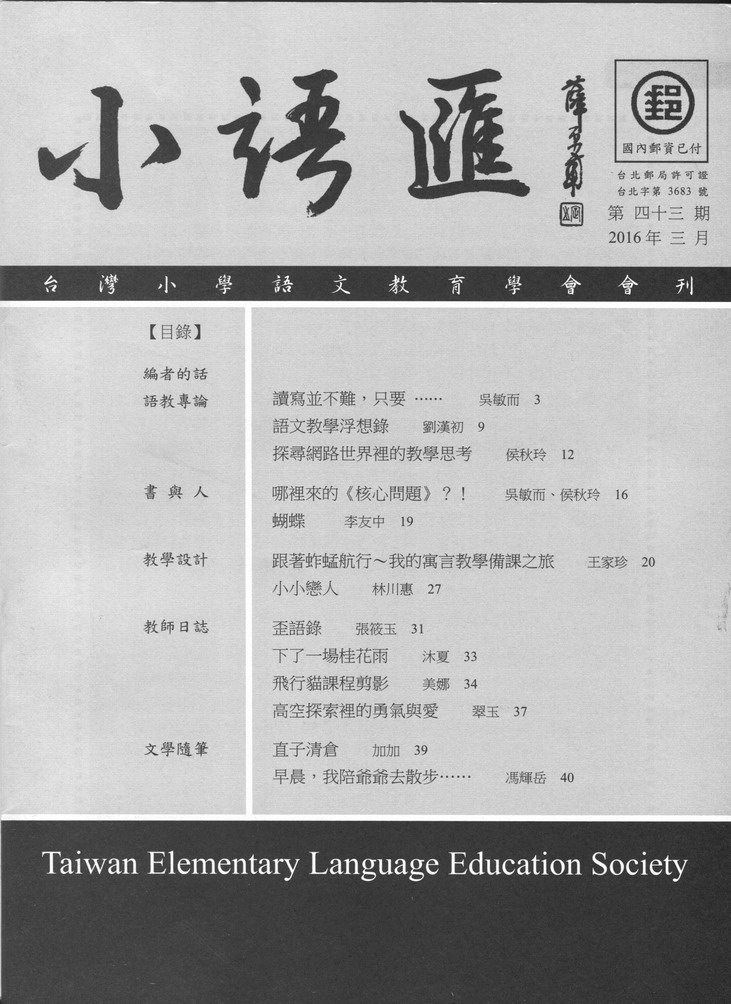
開場白
在學術界混了一輩子,如果說我對理論不感與趣,一定有人覺得奇怪。但事實上我的確喜歡散漫卻滿溢智慧的文章,遠過於嚴謹的學術理論。讀古代的詩話、詞話時,我興高采烈,但讀到什麼結構主義、讀者反應批評,卻真的是「白日欲臥」。多年前受了吳敏而的蠱惑開始弄一點語文教育,就斷斷續續地看了許多、想了許多。最近因某個偶然的機緣,頗有意願把一些想法寫出來,但又討厭寫成學術論文,就採用文心雕龍「浮藻聯翩」的命意,用隨筆的方式,瑣瑣碎碎的談一談,給《小語匯》的讀者一點娛樂,姑且名為「語文教學浮想錄」。
語文教學的四大支柱
嬰孩學語言,從牙牙學語開始,到能講出非常複雜而順暢的句子,他們的學習過程中,從來不會理會什麼叫做主語,什麼叫做受語,什麼叫做詞性,不知何謂辭格,更不知何謂文法,甚至連說得正不正確、完不完整也不去分辨,他們只是不斷地重複說著,不斷地再試,並且碰巧會得自已修正,再不斷地演練、重說。換句話說,他們不要太多的輸入,卻需要極多的輸出。他們當然常犯錯誤,但不要緊,在不斷嘗試演練中,他們自己會找到最好的去路,一方面適合自己幼嫩的思維方式,另一方面又能符合他人的理解層次,也即是可以充分用語言與別人溝通,有時雖然與他人的說話習性有異,但卻甚至說得更為巧妙。這個「不斷地重學,不斷地再試,不斷地修改,又不斷地練習」,是一種毅力的表現,嬰孩何以有這種毅力?那是因為他們十分渴望能與別人溝通,他們強烈地察覺到要表現自己的所思所感,一定要透過聲音來傳達。這是一種希冀掌握語言的接受與傳播的原動力。
依照這個觀察,我們可以說,語文學習的初始階段是很簡單而直接的,它不需要任何所謂「規律」、「模式」,那些許多人深信學習語文必須用到的工具,孩童只要直接吸收在他們周邊的語料,經過有組織或無組織的調配,然後直接表達出來,起先可能說得不正確,但只要給他們足夠的空間和時間,讓他們能夠維持表達的強烈意願,他們終必能夠修正學會。容許出錯,鼓勵再試,引發意欲,激起興趣,是語文學習的四條支柱,比那些強制輸入的工具性規範有用,也有趣多了。
因此,激起學生的這種原動力,語文的教學就成功了。套用時麾而又有趣的講法,這種原動力,可說是學生天生具有之語言的原力( the Force),教師是尤達(Yoda),是歐比王(Obi-wan Kenobi),絕地武士(Jedi)的訓練與養成,從來不在技術層面的枝枝節節(如劍術,如射擊,如輕功,對學生來說是筆順,是詞性,是句式,是文法修辭),他們重視激發對原力的感應和催動!
所以說,低年級的教師們最好多多思考,讓學生乖乖地聽你教完語文課,接受你強制輸入的種種語文工具呢?還是設法讓孩子們有表達自己的衝動(說話)呢?如果以課文涉及的語意範圍經營一個開放性的場域,教師設法引起孩子們對這場域中的相關意念作出感應,然後誘導他們說出因這些意念引起的種種感覺和想法,容許出錯,鼓勵再試,引發意欲,激起興趣,這會不會更有趣和更有效果呢?在我看來,尤達大師訓練路克天行者就是這樣做的。建議教師們找出星際大戰這個經典片段重溫一下,或者會得到更多的啟發。
附記:四大支柱不應只適用於低年級,十二年國教都應合用,這些觀念有機會時再談。尤達的名言:「做或者不做,是沒有『試試看』這回事的。(Do or do not. There is no try.)」希望教師們多多努力。
聰明的機器與語文教學
去年十二月初,第十四屆兩岸四地語文教學交流會在重慶舉行,我們這一梯次十多人先到成都訪問,在臺北松山機場集合出發。當天大家到得很早,枯坐候機室中多時,百無聊賴,有些人隨意走動,不久就湧起一股購物暗流,女老師們去看圍巾皮包,許學仁教授卻去買汽水。
他把一個十元硬幣,兩個五元硬幣投入自動販賣機裡,汽水沒有出來。他按鈕退款,出來的卻是兩個並非原件的十元銅板。這下子許教授可興奮了,逢人就講他這番奇遇,說這麼聰明的機器真是少見。
我們都猜測,說不定這部本來很呆瓜的機器裝了什麼電腦軟件吧,居然會辨識轉化,吐出兩個和原件不同的硬幣。正說話間,我忽然像觸電般想到,大家都關心的語文教學,豈不是也應該這樣的嗎?
我們教學生什麼,不是只期望他記住原樣而已,而是企盼他把學到的東西,充分了解吸收,逐漸完成內化,或者經過時間和情境的推移,沈潛在意識之中,然後往多方向轉動生發,到了適當時機把相關的印象一一喚起,變成很不同的樣貌,很不同的內容,再表達出來,就像這部聰明的機器一樣,出來的會是些不一樣的東西,但卻的確是從所學的轉生而來的!
我們常常看到,許多老師十分著緊教學生造句,有時是依著句式造,有時是依著特定詞語的特定意思造,為了讓學生有正確的理解和應用,這樣的教學當然無可厚非。可是如果學生一直沒有學會,或是沒有造對,那可怎麼辦呢?
這個問題其實不用過度憂慮,依據我們在上期提出的螺旋式學習原理,只要學生在往後的日子裡,重複遇上這些詞語或句式,為了要明白所接觸的語言的意思,他自己會設法弄清楚的,到了偶然時機來臨,他也會不經意間用上這些詞語或句式,雖然和你教的可能有點距離,但未必就是錯誤,有時甚至更有新意。譬如說,你教量詞使用,用「一條毛巾」、「一條馬路」作例子,學生也許會寫出「一條雲彩」、「一條細雨」這樣看似不合理的東西,但假如你深入想一想,學生恐怕真的很懂「條」這個量詞在形象上的意涵呢,他超越了「條」作為文法或詞性用語的範疇,儼然是文學作家的寫法,這樣的學習成果好極了。
因此,不要迷信所謂語文的「正確」理解和應用,而是多注意學生寫出來的東西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些另類思維,而且這個思維別有新奇的意味。太過執著於所謂「正確」的語文,有時會扼殺了學生的創造能力,最低限度也壓抑了學生對語文的學習興趣。我們講模糊理論的重要,目的在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