語文教學浮想錄
文/劉漢初 小語匯第四十四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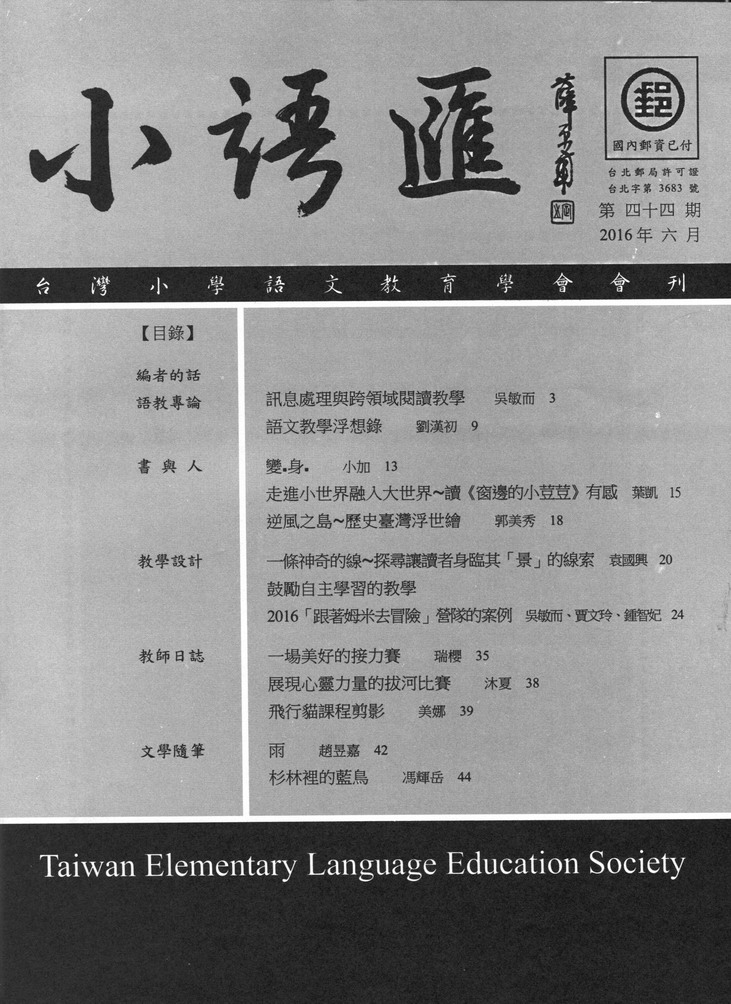
語言的魅惑力量
回顧過去四十年的國語文教育,許多人會覺得,這是一個長期持續的衰退趨勢,特別是最近十年,從小學生到大學研究生,國語文能力更如奔馬下坡,情況不妙,讓人不安。大家好像都知道問題在哪裡,可是都拿不出有效的對策。這件事千頭萬緒,牽涉的層面深而且廣,看來不容易規畫得出一套精密可行的改善辦法。現在姑且提出一個小小的意見,讓大家深人思考一下。
目前國語文教育成效不彰,最關鍵的問題可能在「興趣」上面。幾年前一個在高中教國文的學生告訴我一件驚人的事,她接了一班高一導師,第一天上課就問全班,每人都喜歡些什麼科目,問到國文時她還滿懷期待,設想那些孩子定可以好好調教。但是,全班沒有一個舉手!再問一次,所有人還是寂然以對。到在我仍清楚記得,她說這事時的驚怖神色,真是不可思議!
我在香港長大,記得中小學同學之中,好像沒有誰討厭國文課的,最多是不十分喜歡而已。要知道,那時還是相信背書是最佳學習方法的年代,進了中學,所有文言文都必須背誦,包括全篇的大學、中庸,荀子勸學、莊子秋水,至於什麼〈愛蓮說〉、〈岳陽樓記〉、〈出師表〉,那是小點心罷啦。有時在課間自己記誦,同學越念越大聲,大家似乎在競賽,最後往往是興高采烈,背書竟然不是苦事呢。不過大家從來不背註解,考試時老師只要求寫出語意大要,通達即可。老師講解文章,遇到好的意思,不忘多加點撥,在文學性強的地方,也會特別提出,引導學生感受。最有趣的是,老師往往隨時插入些課外的歷史故事和名言妙對,使人大感興趣。我至今還記得許多,像說到曾國藩和左宗棠(字季高)政見不合,有一回吵嘴,曾出了一個上聯要左作對,說「季子自視甚高,與我議論常相左」,拆開對方的名字造句,分明要他對不上,但左宗棠大有才學,應聲即說「藩臣以身許國,問他經濟又何曾」,果然棋逢敵手。至於像過年的春聯,什麼「急急忙忙一腳踢出窮鬼去,歡歡喜喜雙手捧進財神來」之類,聽了令人精神一振,覺得語文真的很好玩。可以說,國語文我們是玩著學的。
無論小學中學,當時都重視成語學習,同學們不約而同地都找些成語故事來看,所以,我們從小就知道許多歷史人物和小說角色,也因為他們的事蹟所以知道一些中國文化和思想,當然更知道好些文學作品。老師也喜歡在黑板上寫些古詩給大家講解,許多同學順便就把它背下來了。這些資源日後都成為我們說話作文的好材料。
我們學國文實在非常起勁,當時大家都不去管是什麼道理,只覺得這裡面有很大的樂趣。那些樂趣是怎樣來的呢?我認為是語言的魅惑力量使然。那些含意精巧,詞句奇妙的語文,讓人賞心悅目,不知不覺就貯積胸中,以至於摹仿轉化,進而變成自已高超的表現能力。
我們或者可以想一想,怎樣把語文課變成很有趣的教學?要不要拋掉那些枯燥的語文常識規範?減少照樣造句那種呆笨的練習?讓學生嘗試天馬行空的運用語文,玩弄語文?教那些怎樣都學不懂的唐詩之餘,也講一些「江上一籠統,井上黑窟窿。黃狗身上白,白狗身上腫」(雪詩),好不好呢?
文章小意
這個題目完全出於杜撰,是相對於「文章大意」而言的。
大概自有語文教學以來,講文章必絜舉每一段落的大意,再提煉出全篇的主旨,要求學生明白記住,認為這是講解文章的首要任務。有些教學手冊甚至不曾講述每段的意思,就直接以三四句說明全文的大意主旨。這在中學國文最是常見,小學則可能是因為課文的主旨太簡單,沒什麼好說的,因此著重字、詞、句的教學。可是,大家似乎都忽略了「文章小意」的重大作用。
什麼叫做「文章小意」?直白的說那就是文章的細節。不過這裡更偏重指一篇文章中,某些特別能夠呈現微妙意義或精巧情趣的語句,它通常只是全文的一小部分,但如果你忽視它,那就好像畫龍卻不畫眼珠子,這條龍就顯不出精神活力,有如死龍一樣。《世說新語·巧藝篇》記載,東晉著名畫家顧愷之畫人,畫好了卻留著眼珠子幾年不點,有人問是什麼緣故,他說,人的手足四體,是美是醜,無關於妙處,傳神寫照,卻正在這個裡頭。可見無論寫文章或講文章,找到可以著力的「眼」很重要,而這「眼」,就是這裡要說的「文章小意」。
還是用實例來說明吧,大家都知道漢樂府〈江南〉這首詩,自古以來人人都說這詩好,我們讀來也覺得活潑愉快。但是,〈江南〉好在那裡?「江南可採蓮,蓮葉何田田,魚戲蓮葉間。」作者寫到這裡,是不是把意思都寫完了?後面的魚戲蓮葉東西南北,不就是「魚戲蓮葉間」了嗎?他重複再寫豈不太煩了?再說,我們教學生作文,都告誡他們不可用詞重複,可是這篇〈江南〉完全顛覆了我們的認知,他的重複實在太超標了,但,這詩的好卻全在這裡!
面對一首詩,覺得它好卻不知好在那裡,要解決這個問題,最有效的做法就是「自問自答」。前面講的是第一個疑問,第二個疑問是,為什麼詩中說的方位順序是東西南北,而不是我們習慣說的東南西北呢?這就要進人解詩的第二個方法——「設身處地」。我們就化身為一個遊人,划一條小船,在江南水鄉中看採蓮看游魚吧。你看這些魚呀,才在東面游著,卻一忽兒竄到西面去哪!剛游到南面去了,怎麼轉眼間又竄到北面去了呀!這可多有活力,看著令人愉快呢!這首詩非用重複語不可,因為重複語的一個效用就是誇張,就是強調,這四句一出,我們就覺得這魚可真多啊。如果游動的方位是東南西北,那就是循序游了一個圈子,給人的感覺是悠悠閒閒的,就沒有多而熱鬧的那種勁道了。
當年編實驗教材,我們就很注意這「文章小意」,像寫到〈巫婆瑪姬〉,我們就刻意誇飾老巫婆的飛行姿勢和方向,把它寫得很富形像,而且很有勁道,這樣,瑪姬的萬里追尋才更顯意義。又如寫〈水鬼〉,那些對話有許多細節,既暗示水鬼和漁夫的善良德性,更顯示兩人在互動中各自流露的體諒與交情。其他像〈黑狗和花貓〉,黑狗捉老鼠的場景之所以那樣誇張和錯亂,目的就是表現不能適才適所的荒謬與失敗。總而言之,一篇文章的活力,最需要在小意上表達,集合許多成功的小意,文章才顯得有趣味。教者如果常常注意這些,一定可以提高學生學習的興趣,進而讓他們喜歡國語文課。做人不拘小節固然好,教學卻不能不拘小節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