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「學校—教師」遇上教育改革
文/趙鏡中 小語匯第四期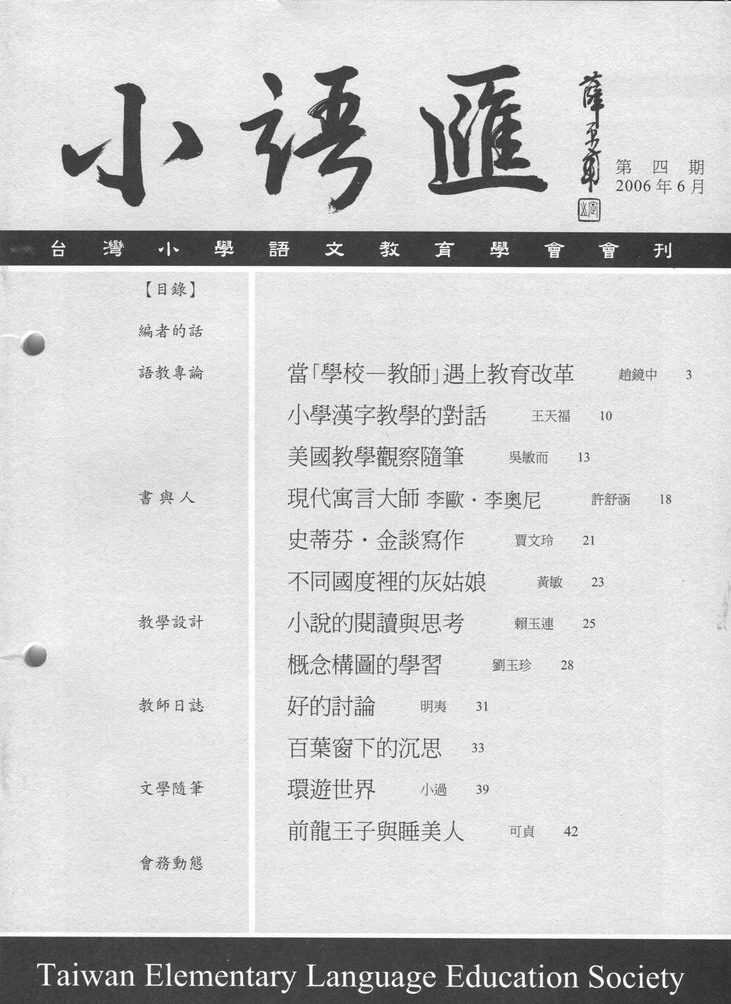
一、開場
(一)、尋找發聲的角色
舞台已搭建好,戲也已開鑼,各組演員早就迫不及待的粉末登場了,看著這齣教改大戲正緊鑼密鼓的上演中,但仍有許多「學校一教師」卻仍找不到自己的發聲角色。有點遲疑;也有點失落,更多的是無奈。遲疑是因為對這齣教改大戲的戲碼不是那麼的熟悉,失落是感覺到從事教育工作這麼些年,卻彷彿仍是個圈外人,甚至成為改革的對象。而無奈是面對政策、家長、專家、學生的權利拔河時,卻只能狗吠火車般的在一旁坐視。
到底在這齣教改大戲中,「學校一教師」要扮演個什麼有利的(此利非利益的利,而是一種有意義參與,以及有著力點的參與)角色,讓自己不只是個局外人或旁觀者。當很多「學校-教師」還在思索時,鑼鼓喧天中隨著各路演員角色更替,上台的上台;下台的下台,一陣的混亂中不自知的已被擠上了舞台。樂聲響起,台上的演員、台下的觀眾,都圓睜著雙眼緊盯著瞧,有一些看熱鬧的意味,也有一些看門道的睥睨……。
尋找自己發聲的角色,成為「學校—教師」參與這齣教改大戲中關鍵的選擇。
(二)、好戲開鑼
場景一
「教授!」一位國中二年級的學生很困惑的問,「你教我們這些閱讀的策略:怎麼分析角色;怎麼比較觀點,是很有趣,但是和基本能力測驗有什麼關係?」
「……」教授搖頭,無言以對。
場景二
「這節課我們要來上四大句式,」國二老師發下講義後,對全班說:「先看敘事句,敘事句的標準句型是:主語+述語(V)+賓語(受詞)。簡單說,有動詞就是敘事句。像我讀書;貓捉老鼠;故人具雞黍;這些都是敘事句。要注意喔!去年北一女推甄就有考這題。」
場景三
在教師研習課上,有位老師說:「現在國語課減少為每週只有五節課,時間不夠,很多活動都不能做,以前至少還有八節課……」
教授有點疑惑的說:「可是,以前老師們也都在抱怨時間不夠啊!?」
場景四
另一個研習會場,教授提到評量的意義,教什麼就考什麼,每班老師應可以自行命題。一位老師站起來說:「我們鄉下學校,家長很重視分數,考試一定要公平,所以各班教的要一樣,考的也一樣。」
「考卷是誰出的?」教授問
「出版公司出的啊,他們都編好了。」老師答
場景五
有一位教學相當認真的老師私下說:「自從九年一貫實施什麼『班群』、『協同教學』後,老師教學的空間和彈性反而變小了,想做一些適合自己班上的教學活動,還必須和協同的班級;甚至全學年溝通,大家一定要做一樣的才可以……,唉!這算什麼……」
二、「學校一教師」與課程改革
教改中的關鍵因素是課程改革,而課程改革的場域無可避免的是鎖定在「學校—教師」身上。但課程改革的主體是誰?政府、社會還是「學校—教師」?(就「學校—教師」此一概念分解的來看,還是要問同樣的問題,改革的主體是誰?學校?還是教師?)必須先弄清楚。誰作為改革的主體,所編製出來的故事自然不一樣。
(一)「學校—教師」如何看待「課程改革」?
若教改的主體是政府或社會,則「學校-教師」成為被改革者,大勢所趨下,「學校—教師」只能偃兵息鼓。或是虛應故事;或是提早退休;或是茫然不知所從,不安的徵詢當局者或專家學者該怎麼做?怎麼做才對?而主事者及專家學者也多從績效主義的觀點,或是一己之見,指點著的「學校—教師」按統一的標準、模式來進行改革。主事者及專家成為推動教改幕後的黑手,形成同一模式不斷複製的一窩蜂現象。
若教改的主體是「學校—教師」,那是一種自體演進的正常歷程,變革本就是社會、生物發展的自然趨勢,因此來自「學校一教師」自主的改革,就能見鬼打鬼、見佛拆佛,無往不利,終能調適上遂。
然而,促使「學校—教師」自體演進的反省機制何在?憂「德之不修,學之不長」的君子之憂(憂患意識)早已不復存在,連最基本的職責倫理在價值混亂的環境中亦無法要求。另一方面,教師對於自身的專業不願堅持,甘願淪為考試的工具,而仍口口聲聲的說是應家長要求。如是則「學校一教師」的主體性如何挺立?「學校—教師」的教改運動不比農民或勞工運動,基本上不涉及生命存亡的基源問題,只是意識層面的價値問題。反省機制如何活絡;專業如何堅持;熱情如何延續,成為「學校—教師」自主性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。
(二)「課程改革」如何對待「學校—教師」?
此次課程改革中所強調的「統整課程」與「學校本位課程」,可說是符應了知識社會來臨的趨勢。相對的,對傳統的課程也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解構。換個角度來看,也可說是對「學校—教師」一種增權(權力下放)賦能的過程。
所謂「統整課程」可視為對知識結構與分類的重新思考。
所謂「學校本位課程」可視為對組織文化與價値的根本顛覆。
這兩項對傳統課程結構的適度顛覆與解構,確實能將教師從「教書匠」、「教育下游操作員」的魔咒和困境中解放出來。但令人困惑的是,大部分的「學校—教師」卻又拱手將專業自主的權利交還給政府或專家學者,甚至是出版商。
當教改透過制度來實踐這一解構過程,也引起既得利益團體(如書商)的阻抗,以及第一線教師的疑慮。阻抗是為了保衛利益,疑慮則來自於習性的衝突與陌生。而這都需要透過良好的溝通協調和政策宣導(諷刺的是:知識社會所重視的溝通能力,在教育單位卻付之闕如)以及有效的成長研習,來逐步調整。
三、「教改」還是「叫改」?「推手」還是「殺手」?
從知識的重構到組織的變革,此次課程改革幅度不可謂不大。因此,需要更多的支援措施,如新能力的培訓,新觀念的溝通,新資訊的獲得等,但最重要的支援則是時間;「學校一教師」需要充分的時間來重新調整權力結構,培養互信與溝通的基礎,以及從傳統的學科架構中解放。然而,弔詭的是教育改革最缺乏的往往就是時間,因此要求短期(具體)績效的當局,一方面是推動教改的「推手」,一方面卻又成為扼殺改革的「殺手」。
撇開時間的因素暫不談,在這樣一次由上而下大幅度教改的工程中,「學校—教師」所面臨的改革障礙還包括:
1、教師本身心智習性的調整
2、教師缺乏合作的
3、專業成長研習模式的僵化
4、學校執行政策的偏差
5、「學校-教師」過多的行政負擔
6、學校與家長過度重視考試成績
以下只就教師專業成長的「忙與盲」及行政機制的「任我行」,兩個關卡進行反省:
(一)教師專業成長的忙與盲
專業成長的目的有二:一是幫助教師認知與調整自我的心智習性,以利教學。二是協助教師與最新教育理念接軌,與社會同步。專業成長與養成教育不同,基本上是假定教師已具備教學相關知能,在此基礎上尋求更專業、更優秀,進而能成為教育改革的主體與內在動力。
然而,現今的成長研習模式似乎並未從此方向來設計課程,仍然是將教師當作是教學工具,研習課程中充滿了政策的宣導與技術層面的教學技巧示範。令人扼腕的是,教師似乎也滿足於這樣的研習模式(還是敢怒不敢說)。因此,專業成長並不能真正帶動教師與新教育接軌。再者,在專業成長的過程中,若干教授專家往往無意中透顯出一種學術與專業的傲慢,讓教師敬而遠之。總括的說,專業成長也是一種學習(如同課堂裡教師與學生的關係),因此研習的模式不應與教學現場脫節。換言之,希望教師如何對待學生,就應在研習時如何對待教師,模式應該是相同的。
(二)行政機制的「任我行」
新課程改革中強調學校本位課程,意味著對傳統組織文化價值的重新檢討。然而在實施的過程裡,看到的都是針對教師教學的檢討、改善,鮮少針對學校行政著手改造。每所學校均標舉著學校願景,勾勒著教師、學生圖像,但是這些願景與圖像的推動需要的是行政的支援,如果行政組織還浸泡在老機制丶舊文化中,那改革的前途是堪慮的。從比較行政與教學的研習場次,以及各類的研習活動中,行政人員的冷漠與不參與,可以看出整個改革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:重教學;輕行政,而非雙軌並重一步到位。
四丶與「學校一教師」一同成長
(一)另一個發聲的管道
在這次教改大戲中,筆者充其量只是一個曖昧的第三者,或是關心的半個圈內人。圈內指的是自己從事的正是教育研究的工作,但在這齣戲裡只能算是半個圈內人,因為個人既不是主導政策的官僚體系,那算是導演的工作。也不是側身「學校—教師」行列裡的一員——這次教改大戲的第一男女主角。頂多只算是政策下游的執行者,打打雜、檢檢場罷了,甚或是一個無力的家長。
就此曖昧的第三者(我個人)觀點來看:「學校一教師」在課程改革的過程中,充其量只是化學反應裡的催化劑;不能改變化學反應的方向,但能加速或減緩反應的速度。
(二)從「探索的教師」、「思考的教室」開始
舌雖如此,但「學校-教師」仍不可忽視自身的力量,催化劑終能加速反應的速度。問題是我們將期待什麼樣的教師、教室與學校,來回應社會對教育改革的呼喚呢!
這些年參與若干學校的教改工程,歸結出兩個不一樣的取向:一是從上而下的模式(Top-down),由學校行政主導的課程改革。一是由下而上的模式(Button-up),教師自主的成長、改變。這兩種取向,前者雖然一時間光彩亮麗,但往往人去政息,船過水無痕。後者雖然短時間看不到亮眼的成效,但卻因靈根深種,終能開花結果,即便是他/她所能影響的層面可能很小,但絕對是很深刻的。
戲曲終會落幕,但教改的路上,絕不會冷場,一齣齣新戲將會不斷的推出。不管戲碼如何,唯有具備「探究精神」的教師,才是所有教改大戲裡的真正主角。此處所謂的「探究教師」是指一位具備反思能力的教師,也是一位純熟的教師。「探究教師」在教學上會展現出以下三方面的特色(Hendersoner,1992):
‧關懷的倫理
認可、發現學生自身的資產和喜好。
師生之間真誠丶開放的溝通、對話。
‧教學的建構論
視學習為一複雜的歷程,需要將學科主題與學生的背景、需求和興趣連結在一起思考。
‧創意的問題解決
想辦法讓學生投入,讓學習更有意義(具啟發性又很有趣)
教學需要關懷(關懷學生,關懷自己),而關懷會驅動探究和反思——探究學生、教師和學科內容之間是否能有更好、更具意義的連結。因為探究教師將「教」與「學」視作「不確定」的歷程,而不是一層不變的複製,或一些標準化的技術。此外,探究的教師亦具備有豐富的知識,他們並不否定專業知識的概念,只是他們對知識基礎的形成更傾向於自我建構——建立起屬於自己的、個人化且具擴展性的專業教學知識基礎。
總括來說,探究教師具有以下特質
1、面對複雜的教育現象、問題,能以多種方式展現其專業能力。
2、在時間管理上、生活常規上、教導方式、人際溝通及學習理論等方面都具有專業的看法。
3、能偵測出困難發生的起點、原因,不輕易慌亂。
4、透過反思的練習,發展出做決策的自信與技能。
5、經常反省行動的結果。
6、從不停止嘗試,持續在反思中學習。
這些特質正是現今大多數教育工作者所欠缺的。由探究教師所帶領的課堂學習,將呈現為一思考的教室,師生所共同關心的不單是學科知識的學習;不單是思考技能的學習,更關心的是心智習性的養成與思考文化的浸潤。這種以文化為主(culture-based)的教學模式和傳統以主題為主(topic-based)的教學模式是相當不一樣的,主題為主的教學通常用來教學生事實、知識。而文化為主的教學,則著重學生良好習生與關鍵力的培養(Shari Tishman, David N. Perkins & Eileen Jay,1994)。
一個學校如果能植基於「探究教師」與「思考教室」的培養,面對任何教改的衝擊也必能呈現出創意的氛圍,在這裡一切都是可能的,因為教師的信念是學校改革的核心所在,學校成為教師的舞台,教室成為學生的舞台。學校願景、統整課程乃至學校本位課程,均可經由探究教師們的探索而形成,它們不再是虛應故事或遙不可及的空泛口號,不再是窒礙難行的課程枷鎖,也不再是受家長考試取向牽絆的扭曲教學。
當然學校必須給予教師、學生長期及持續性的肯定與堅持,否則一切的改革都將成為「三分鐘熱度」症候群的犧牲品。因為學校領導者及行政人員強烈的影響課程與教學,即使他們並沒有每天在教室裡授課。行政人員應持續的對教師、學生彰顯學校的價值體系,畢竟核心價值是需要透過欣賞和讚頌而傳達的。
最後,要感謝許多學校的邀請,允許我參與學校的教改工程,而有了以上的一些體悟。更感謝的是容忍我這一個不是很清楚路程的嚮導,帶著大家跌跌撞撞的往目標前進。也許多走了一些冤枉路,也許多摔了幾次不必要的跤,這一切看在我眼裡,真的感覺到很抱歉。唯一能讓自己略微釋懷的,就是自己是很認真的在做這件事,也因為認真而讓這個過程變得有意義而值得了。目標仍在前方,我們還是要繼續往前走,回首走過的路,讓我們更堅強,也讓我們更同心協力,而我這個嚮導也學到了要走走停停,讓大家多些時間瀏覽沿途的風光,而不是一昧的趕路,畢竟過程是比結果重要的。
本文發表於「兩岸七地教育研討會2006」